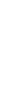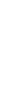渣了高冷校草以后 - 第30章
许慎毕业后,每个月的工资要拿出一大部分帮许父还债,也很难有所积蓄,那一阵子他对展新月非常歉疚,幸好新月并不在意这些,爸妈也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后来展巍年纪渐大,店里的生意顾及不过来,是许慎主动辞了工作,去店里帮忙。说到底,以后这些生意到底还是要留给新月夫妻俩,所以爸爸也乐见其成地给了许慎一间店让他学着管理。
许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第一年赔的很惨,展巍却没说过什么,亲自到店里带他,手把手地指导。许慎也确实有毅力,肯吃苦又善于总结,很快就扭亏为赢,后来彻底接管了展巍的生意。
昨天夜里,展新月忽然想清楚了很多事。
展巍虽然后期生意做的不错,但他不想再事业上投入过多的精力以致于无暇顾及家庭,所以后面并没有再扩展店面。但许慎不一样,他更进取,更有野心。全面接管生意以后,他不断尝试新的投资,加盟扩张。短短几年,他不仅轻松地帮父亲还清了外债,还让家里的资产直接翻了十几翻。
她想起城郊的那处豪宅,那时的他已经可以轻易买得起昂贵房产,还可以养得起小三和私生子。展巍要是知道了这些,是否会后悔当年对他毫无保留的倾力相授呢?
家装店是展巍的心血,重来一次,展新月不会再放心地将他的奋斗一生的成果拱手任何人,更不会让老爸亲手打拼出的一切,成为别人刺向他唯一女儿的一把利刃。
第25章
第二天到了教室,展新月还没来得及找机会朝谢宛之打听时子骞的事,她自己先凑了过来:“新月,你昨晚放学怎么走那么快,值日都忘了。”
展新月闻言扭头一看,教室后面黑板角落里代云手抄的一周值日表,昨天的方框里果然写的是她和谢宛之的名字。
她才想起,班上似乎是要轮流值日的。不过因为每天就只排两个人,很久才能轮到一次,她对此印象非常淡。周一代云写完值日表好像提醒过一回,但她没太注意到。
“我忘了。”展新月说,“你最后一个人做了吗?”
谢宛之停顿了一下,朝着展新月身旁空着的位置看了一眼,说:“也没多少活,我一会儿就干完了。”
她这样轻描淡写,反而让展新月更加不想欠她这么个人情。想了想,她说:“这样吧,下次轮到我俩值日的时候你就不用留下了,我一个人干就好了。”
“咱俩说这些就见外了哈。”谢宛之一把揽住她的肩,这才多大点事啊,小意思。”
陆蒙转过头,面露赞赏地看向她:“您可真是当代雷锋啊,话说这位雷锋同志,明晚我值日,您看……”
“去你的!”谢宛之抄起一本书,在他头上敲了一记,“你要是男人你就该说以后我们的值日你都包了。”
陆蒙一边闪躲,一边大言不惭道:“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男人了。这位同志,小生今年才17,还是男孩子一枚呀。”
“呕,你恶不恶心。”谢宛之和辛文华同时发出一声干呕。
几个人吵吵闹闹了一阵子,谢宛之在和他们打闹的间隙飞快又看了眼展新月身旁的座位,眼神有点飘忽。
其实昨天晚上,她并不是一个人做的值日。
昨天晚课结束后,谢宛之咬着笔磨磨蹭蹭地终于写完学案上最后一道大题,舒展了一下身体,才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招呼:“新月,别忘了今天……咦,人呢?”
每天晚课后班上要有两个人打扫卫生,当晚是她和展新月两个人值日。这排序还是之前她俩私下找了班长,专门把两人排到同一天的。
这会教室里已经没多少人了,展新月位置上空空荡荡的,半个人影都没有,就只有旁边时子骞还在位置上坐着。
谢宛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人去哪了,不会走了吧?”
她原本想着展新月虽然右手不方便,但好歹可以擦下黑板扫扫地分担一些,她再做些别的,两个人很快就可以弄完了。但要是展新月不在,这些活她一个人就得干上好一阵子。
她不死心地朝着展新月的座位走去,靠近时见时子骞还在位置上,少见地似乎在发呆。
谢宛之不由地放缓了步子,有些拘谨地走过去,时子骞一只手支着下巴,微垂着的眼睛眼睫漆黑,透着拒人千里的冷淡。
她迟疑了一会儿,又探头看了看展新月的桌子。
展新月桌面上的书都合着,笔袋也拉着,显然是真走了。
一会儿的功夫,教室里刚刚还磨蹭着没走的几个人也已经走光了,谢宛之环视教室一圈,辛文华陆蒙也早就溜了,这会儿是一个壮丁都抓不到了。
“唉,得了,一个人也靠不住。”她自言自语似的,“还是自己干吧,我可真命苦。”
说完,她又看了看满教室横七竖八的桌子,不禁有点恼意,伸手忿忿地掀了一下展新月桌面上的书,小声嘀咕:“真服了,这什么记性,连值日也能忘,这让我一个人怎么弄得完啊……”
旁边,一直在看书的时子骞缓缓侧了头,抬眼意味不明地看向她。
明亮的白炽灯下,一张原本就很惊艳的脸五官更加清晰深刻。
她下意识地噤了声。
他却已经合上书,站了起来。他个子高,起身时压迫力十足,让谢宛之不由地往后仰了一下。
“我来吧。”时子骞说。
谢宛之张了张嘴,轻轻“啊”了一声。
教室里空空荡荡,前后门都大敞着,门外夏夜里的蝉鸣一声高过一声。
时子骞就站在她面前,垂着眼看她。他的眼睫很黑,注视着什么时总会给人一种极专注的感觉。
“我来值日吧。”他又说。
谢宛之有点晃神,拢了拢头发,不敢确定地小声问:“你是说,你要跟我一块值日吗?”
“嗯。”时子骞依旧看着她,“需要干什么,分一下吧。”
一直到时子骞半挽起袖子,站在讲台前面准备擦黑板,谢宛之都感觉有点恍惚。
时子骞,竟然主动提出要帮她值日?
听起来非常不真实。
班上的值日表代云之前有排过他吗?她记不太清了,但她实在是想象不出时子骞这种一看就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值日的样子。
教室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时子骞自刚才之后就没再说过别的话,顾自去了讲台上。谢宛之站在教室最后面,悄悄对着他的背影上下打量。
谢宛之其实很不喜欢擦黑板,每次总要弄满身满头的粉尘,而且总是需要搬椅子踩着才能擦到黑板的最上沿。
时子骞自然不用,他拿着黑板擦手都不必完全伸直,几下就利索地擦完了大半。她能看见空气里微小的粉尘从前排弥散开来,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会在擦黑板时下意识地摒住呼吸。
等他放下黑板擦回过头,谢宛之才赶紧低下头。她刚刚说自己负责扫地拖地,半天了都还一动没动。
教室后面放着小桶,她去取扫把时瞥见昨天不知道是谁值的日,用完小桶脏水都没倒,没洗的抹布脏兮兮地漂浮在水上,像泡肿了的尸体,透着一股恶心劲。
时子骞已经从讲台上下来,朝着教室后面走过来。
谢宛之连忙皱着鼻子小声嘟囔了一句,企图掩饰自己半天了一点活还没干的尴尬:“这谁这么没素质啊,用了抹布也不洗,好烦。”
想了想,她又说:“昨天他们肯定没好好干,明早我让他们自己去洗,我们就别管了。”
时子骞没接话,路过她时一伸手就将那块脏兮兮的抹布勾了出来,稍微拧了拧,而后提起水桶出了教室。
“啊,太脏了,还是我来吧……”谢宛之在他身后徒劳地补了一句,没收到回应。
他走出去以后,谢宛之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环视一圈,忽然有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扫把被丢在角落里,她看了看,终于捡起扫把开始扫地。
卫生间零星有几个洗拖把的同学,时子骞在最边上站定,先将桶里的脏水倒了,又开始洗抹布。
那块黑黢黢的抹布在水龙头下冲了好久才稍微能看出来原本的颜色,看起来它绝对不只是昨天没被洗过,已经不知道被丢在那里泡了多少天了。
指根在触到抹布污脏的黑水后传来一阵钝痛,时子骞将抹布拧干搭在一边,又摊开手掌对着流水冲了冲。
手指上刚被烫过的伤痕被流水冲过,刺痛感无可回避,重新勾起在天台上的记忆和彼时她风轻云淡的话语。
时子骞盯着流水看了很久。
镜子中照出昏暗光线里他的身影,镜中人跟他一样,视线沉沉,显出很深的茫然。
自时子骞出去以后谢宛之就一直在发愣,拿着扫把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等到她视线忽然瞥见时子骞的身影从窗口一闪而过,才连忙弯下腰,开始认真扫起地来。
时子骞提着干净的水进了教室,又回到讲台上用湿抹布擦第二遍黑板。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